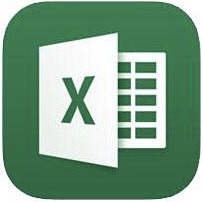新闻
“劳动力短缺”威胁已至,船舶工业路在何方?-空运价格
海运新闻 | 2019-07-04 08:48长期以来,较低的用工成本一直是我国船舶工业相较于其他主要造船国的核心比较优势。但是,近年来,早前已逐渐浮出水面的“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呈现出愈发严峻的态势,不仅给越来越多的骨干造船企业造成了困扰,也引起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重视。

人口红利衰减 船企遭遇“用工难”
根据多家骨干船企反映,目前,船舶工业劳动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工人流失严重、工人年龄明显偏高以及用工成本高。当前,船企用工以外包工为主,本身流失率就比较高,加上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中西部省份,其返回本地就业的数量呈增长态势,每年过完春节,船企都会因返厂工人的减少而发愁;船企用工仍然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80后已经大量离职,90后很少愿意到船企工作,导致船企工人的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骨干船企多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平均工资较高,船企及包工队为留住现有工人只能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多数船企劳务工工资已经超过5000元/月,个别地区工资达10000元/月。
实际上,“招工难”“用工贵”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现象。我国经济40多年来的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撑,主要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
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拐点”早已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制造业用工成本的刚性上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28%,却占用了71%的就业人口,表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工厂门口常常是人满为患,工人们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也推动了船舶工业完成从本工为主向以外包工为主的转变。这个过程持续到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被第二、第三产业吸收,其标志就是工人工资开始明显上涨,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多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因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减少而上涨了15年之久。
适龄劳动人口“拐点”则出现在2013年。之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并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用工成本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2013年,我国15~64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从9.22亿增加到10.06亿,因此,尽管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减少,但制造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并未出现明显短缺;从2014年开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进入了下滑阶段,并在2017年加速下滑,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的程度不断加剧。
更为重要的是,在不断减少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存量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以家政、餐饮、快递等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张,制造业工人不断被分流。2018年,第三产业已经吸收全国46.3%的就业人员,而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从2012年的30.3%下滑到2018年的27.6%。同时,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以船舶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吸引力较弱,年轻人更不愿从事这一行业。
此外,我国户籍制度也是造成制造业劳动力萎缩的重要原因。船企工人大多学历较低,在现有政策下很难获得当地户口,不能享受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保障,最终不得不返乡。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工人来说,在家乡就业将获得更多便利。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2015~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连续4年出现下降,反映了中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输出劳动力数量不断下滑。尽管部分船企尝试提高本地工人占比,但本地人一般不愿去船企,而外地人无法获得福利待遇而最终选择离开。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制造企业“招工难”“用工贵”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问题,再加上老龄化问题的叠加,人力资本相对金融资本将更加稀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延缓这种趋势,但不可逆转。
船舶工业作为劳动力密集行业以及危险工种集中的行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劣势非常明显。多名船企负责人表示,如果不采取措施,5~10年后随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船企将很难招到足够的工人维持生产。欧洲和日本都曾因劳动力成本丧失优势而经历了船舶总装建造产业的转出,但在船舶配套、船舶设计以及船舶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维持了较强的竞争力,目前仍然活跃在国际船舶工业领域。
让人担忧的是,尽管目前我国船舶工业规模庞大,但船舶配套和船舶设计等产业环节尚未形成很强的竞争力,自主品牌配套产品和高端船舶设计能力依然欠缺,如果总装厂再转移出去,中国船舶工业能否继续保持竞争力,值得思考。
日韩船企先行 经验值得借鉴
日、韩船企作为我国船舶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造船工人不断减少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下降的过程。但日、韩船企通过多种措施提高效率取得了一定效果。
日本船舶工业“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出现在1990年左右,之后,日本船企就一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日本造船工业协会(SAJ)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船企用工总量(含外包工)从1976年的26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5万人左右,期间,日本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也经历了快速上涨到逐渐平稳的过程。其中,1960~1980年,日本平均工资水平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上涨;1980~2000年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上涨;2000年之后保持在500万日元/年上下浮动(目前合30万~40万元人民币/年)。
为应对造船工人短缺问题,日本船企通过不断优化船舶设计、开展精益造船、大面积引入工业机器人等方式提高效率,年人均产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1修正总吨(CGT)提高到2000年的60CGT,很大程度上对冲了人工成本的上涨。即使是在2000年之后,日本船企依然不断提高效率以应对韩国和中国船企的竞争,目前年人均产出已经超过了120CGT。同时,为进一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日本船企持续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引入外籍劳工。
韩国船舶工业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适龄劳动力人口拐点出现在2000年前后,之后,船企员工数量从2000年的20万左右持续减少到2018年的10万人左右。劳动力成本方面,1970~1996年,韩国劳动力平均工资增长了5倍左右,之后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回落外,总体呈缓慢上涨态势并逐渐趋于平稳,目前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5400万韩元/年左右(约合32万元人民币/年)。
韩国船舶工业出现劳动力问题时的外部环境要好于日本,2000年前后正值全球单壳油船的集中淘汰期,中国经济启动快速增长模式带来巨量船舶订单需求。同时,韩国相对日本仍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造船产能此时尚未大规模形成。在此背景下,新船价格上涨较快,韩国缓冲劳动力带来的压力面临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为应对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的下降局势,韩国船企在生产组织方式上进行改革,通过开创巨型总段建造法、广泛应用信息化工具、不断优化生产设计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通过建立完备的技能培训体系、提升本工占比等方式提高工人技能、稳定员工队伍,本工占比从2000年的20%左右提升至目前的70%。得益于上述措施,韩国船企的年人均造船产出也从2000年的30CGT提高到100CGT左右。
当然,尽管日、韩通过提升生产效率较大程度上对冲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作为完成工业化且老龄化来临的造船大国,除非智能制造达到很高水平而无需人工过多干预,否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带来的各种问题。目前,日本船舶工业的劳动力缺口依然在扩大。2018年,日本政府又新推出引入50万外籍劳工的计划,以解决造船等行业的用工问题;韩国船企本工占比较高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员队伍,但年轻人对船企的兴趣不断降低,产业的长期持续性发展令人担忧,再加上造船市场波动较大,个别年份订单不足时甚至会出现人员过剩的现象,裁人还是留人,难以权衡。
提升生产效率 对冲不利影响
从外部环境角度来看,中国在应对当前“招工难”“用工贵”问题上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一是时间窗口的问题,日、韩“刘易斯拐点”与适龄劳动人口拐点之间有30年左右的缓冲期,而中国只有1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与用工缺口急剧扩大相互交织,局面更加难以应对;二是市场环境的问题,韩国船企在适龄劳动人口下降(2000年)之后面对的是急剧扩张的新船需求和不断上涨的新船价格,而中国船企在2014年之后则面临着新船市场供过于求和新船价格长期低位的不利形势,这就导致船企缺少剩余资本进行生产工艺工装的升级。
从日、韩船企的以往经验看,缓冲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核心是提高人均生产效率,这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劳动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威胁到了生存,企业才不得不倒逼自身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
对于中国船企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提升管理效率。管理提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船企也很清楚自身在哪些环节、哪些部门存在问题,每年都会进行成本倒逼,但很少有船企能够在采购、外包工管理、生产工艺以及营销方面剔除掉不必要的成本,做到现有条件下的最优。
其次,采取措施留住工人和提高工人技能。有些船企建议国家层面能够在户籍改革、职业技能教育和降低社保缴费率上步子再迈得大一些,最好是能够放开东南亚劳工的引入。但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船舶工业,国家需要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人口发展计划等方面考虑。所以对于船企来说,应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适量增加本工数量、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建立工人技能培训体系等。
再次,扎实提升生产效率,这也是应对劳动力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生产效率提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当前船企缺少剩余资本的情况下,很难短期内实现生产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日、韩船企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关键是梳理出设计及生产的薄弱环节和可以改善提升的方向,每年都能够切实补齐一些短板,每年都能够有实际性且不反弹的效果。目前及未来几年,我国船企劳动力成本相对日韩仍具有一定优势,但这种优势每年都在减少;中国船企效率的提升还有时间窗口,但必须每年都有实际进展。骨干船企应结合自身财力和国家相关政策支持,稳步发展自动化工装、提升信息化水平和推进智能制造相关技术的应用,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对冲工人数量下滑和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提高在船舶配套、船舶设计及船舶工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在欧洲、日本甚至是韩国企业已经构建了强大业绩壁垒的情况下,中国自主品牌配套的发展除了脱硫塔、压载水等新型设备,以及通过收购掌握重要关键技术的低速机等设备外,还有很多产品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船舶配套国产化也面临着部分核心部件及基础材料相关技术尚未攻破,或者已经攻破但难以形成批量导致成本较高、推广困难等问题。此外,船舶设计软件、液货船及特种船设计能力以及船企生产工艺流程、信息化、智能化等相关咨询服务业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愿与产业链各个企业就具体问题深入沟通,组织对接行业管理部门、船企、船东、配套企业、核心部件研发企业、基础材料生产企业、设计公司、高校、金融机构等单位,帮助企业对接市场资源和技术资源,探讨可行的商业模式,寻求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合作,扎扎实实推进船舶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构建属于中国企业的业绩壁垒、成本壁垒和技术壁垒。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 千航国际 |
| 国际空运 |
| 国际海运 |
| 国际快递 |
| 跨境铁路 |
| 多式联运 |